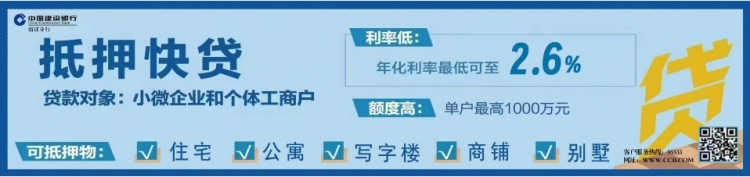
“苏超”烽烟再起,新一轮的对决在“项王故里”宿迁与“东海名郡”连云港之间展开。
当宿迁的醇厚酒香,遇上了连云港的咸鲜海风,这场绿茵场上的交锋,仿佛早已在千年的文脉里埋下了伏笔。

一座城的诗篇,是其灵魂的独白。细品与这两座城相关的诗句,会发现一个极有意思的对望:宿迁的诗,字里行间多是帝王将相的雄心与天下苍生的计较,是一部写在沃土之上的英雄史诗;而连云港的诗,则氤氲着山海之间的空灵与诗意,是一幅浸润了东海朝夕的写意画卷。
这一场对决,与其说是两支球队的较量,不如说是一场“大地史诗”与“山海诗境”的千年对话。
帝王之望:一望麦田,一望仙山
帝王的目光,往往定义了一片土地的气质。有趣的是,两位权倾天下的帝王,在宿迁和连云港,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凝望。

清代,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对宿迁可谓情有独钟。当他立于运河之畔,真正让他龙心大悦的,并非江南常见的“梅柳之色”,而是一望无际的千里麦浪。他在诗作《麦》中挥笔写道:“第一江山春好处,十分梅柳色徒传。”在这位帝王眼中,这片“绿满田”的景象,无关风月,而是“此是千家饼饵计”,是帝国版图上最动人的图景。于是,他严令随行的御林军“羽林驰骑戒纷填”,生怕铁蹄踏碎了这关乎万民生计的希望。乾隆的目光,望向的是脚下这片土地,是人间烟火,是实实在在的江山。

而千年之前,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——秦始皇,也曾驾临连云港的云台山。他站立海边,目光越过惊涛骇浪,望向的却是烟波浩渺处那虚无缥缈的仙山。近代诗人陈凤桐曾有诗云:“嬴政立碑碑石峻,仲尼望海海山幽。”始皇帝在这里立石刻辞,更派遣方士徐福扬帆入海,去寻找那传说中的蓬莱仙境。他的目光,望向的是海的尽头,是凡人世界之外的秘境,是超脱生死的幻梦。
一位帝王低头看麦,心怀天下苍生;一位帝王抬头望海,欲求万寿无疆。宿迁的厚重人间与连云港的飘逸出尘,在帝王的凝望中,早已分野。
文人之思:英雄悲歌,山海入诗
文人的笔,是城市气质最敏锐的触角。他们或凭吊历史,或寄情山水,为两座城刻下了迥异的文学烙印。

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路过宿迁,看到的是“下邳故国经残雨,泗口荒城入断图”。他想起的是两千年前那位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西楚霸王。宿迁的土地,承载的是真实的历史,是项羽这样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,他们的成败与悲欢,引人扼腕,发人深省,是沉甸甸的人间悲喜剧。

而当文人墨客来到连云港,笔锋则陡然一转,将山海奇景揽入诗怀。当北宋文豪苏轼登临云台山,便脱口而出:“郁郁苍梧海上山,蓬莱方丈有无间”,眼前之景瞬间与仙境重叠,壮丽中透着一股出尘之气。而到了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笔下,这片土地更是幻化成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花果山那“一派白虹起,千寻雪浪飞”的水帘洞,不再仅仅是一处自然景观,而是激发奇绝想象的源头。这里的山水,是能让诗情画意恣意生长的绝佳画布。

如果说宿迁的诗是英雄史诗的沉重回响,那么连云港的诗便是山海画卷的浪漫开篇。
一个让人回望来路,一个让人眺望远方。
文脉圣地:入世教化,登高望海
奇妙的是,这两座气质迥异的城市,却都与儒家圣人孔子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并各自建立了一处精神圣地。

连云港有孔望山。相传孔子曾登此山以望东海,故而得名。清代名臣林则徐曾赋诗:“千秋孔望谁能企,聊喜观澜赋水哉。”将孔子这位最讲求“入世”的圣人,与浩瀚无垠、充满未知与想象的大海联系在一起,本身就是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。赵朴初先生更是写下“可能孔望山头像,及见流沙白马来”,将孔圣、海路等巧妙勾连,让这座山的文化意蕴愈发深邃。孔望山,是圣人思考与眺望的地方,是人间哲思与山海想象交汇的渡口。

而宿迁,则有庄严的孔庙。如果说孔望山是圣人“望”的场所,那么宿迁孔庙就是圣人“教”的殿堂。
那座巍峨的大成殿,飞檐斗拱,是儒家思想在宿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的明证。它不再是山巅的眺望,而是融入城市肌理的教化,是礼乐文章的传承,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入世路径。这里供奉的,是作为“至圣先师”的孔子,传承的,则是可学可行的行为准则。

一处是登高望海的哲思之地,一处是礼乐相传的教化之所。连云港与宿迁,竟以这样的方式,完成了对同一位圣人精神的两种不同维度的诠释。
当英雄史诗的厚重,遇上山海诗境的空灵,绿茵场上的胜负已然增添了无穷的韵味。我们有理由期待,这场对决,究竟会是“霸王”式的铁血与坚韧笑到最后,还是“大圣”般的灵动与奇幻更胜一筹?大地与海洋的对话,将在这一刻,于呐喊声中交响。
来 源丨交汇点
编 辑丨张晨红
审 核丨凌 子 驰 骋
终 审丨王军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