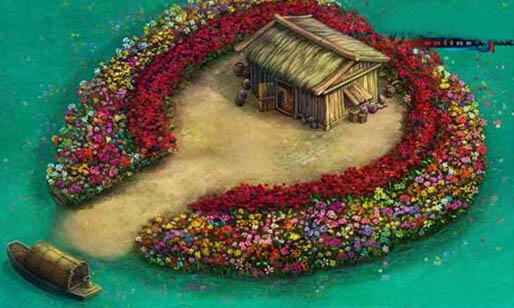
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采访许鞍华的报道,她说:“我喜欢读书和拍电影,它们的相同点是可以使我逃避现实。”看到此话我不禁心有戚戚焉。我的性格、我的生活甚至我日常的所作所为,哪一项不是在逃避现实?有人说武侠是成人童话,我想起了自己少年时的武侠梦了!
可能人生来吃哪碗饭都是注定的。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闲书,开始只看得懂连环画(我们称为小画册),记得当时家里有一本《偷拳》,讲的是杨露蝉装哑巴偷学陈式太极拳的故事。小时候看书不懂爱惜,最后那本小画册被我弄坏了,后来也不知所踪了。
记得生平第一次花钱买书是10岁时的夏天,趁着大人们在午睡,我偷偷跑到巷口的邮电局,用压岁钱买了本《故事会》,不知是故事精彩还是敝帚自珍,总之那本《故事会》我是百看不厌、翻了又翻,最后终于被翻烂了,心想大概“读书破万卷”就这意思吧!
因为家里都是女孩,父母又经常出差不在家,小时候我们被老太(妈妈的奶奶)规定:天黑了就不能随便出院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行动自由度逐渐被放开,开始钻小镇街上的文化馆(图书管理员是我家邻居),去看里面的“大部头”,常常要到天黑关门才回家。就这样,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、岑凯伦、亦舒、琼瑶、鲁迅、矛盾、巴金、雨果、奥斯特洛夫斯基挨个走入我的生活。我发现自己对唐诗宋词蛮感兴趣,虽不能完全领会其中深意,但平仄对仗的用韵,每每读出声,竟有“口齿噙香”的感觉。那时,诘屈聱牙的古文对我不具任何吸引力。
初二时,不知是幸或不幸,我迷上了武侠小说,像吸毒一样,完全被其控制住。梁羽生的《七剑下天山》、《江湖三女侠》、《冰川天女转》、《云海玉弓缘》以及古龙的《绝代双骄》,简直如饥似渴。“飞雪连天射白鹿、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那时的我并未觉出金庸的技高一筹,即便如此,我依然努力寻找着小镇文化馆里的每部金庸小说。我还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----喜欢回味,每部小说看完总需要一两个星期才能缓过神来,回味着武侠小说里的情节,渐渐地,我变了。那段时间,我想当侠女想得发了疯,迷武术到发了狂。三句话里,必有一句是武功招式。那时我的记忆力很是不错,常常不经意间,就把整部小说背了个大概,然后再复述出来。看电视也是第一个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关系。为此,老太说我“知古老道经”、奶奶说我“整天讲古、南朝北物的”。(在淮安念书时,我用三天的课余时间、在女生宿舍里操着纯正的“宿普”、眉飞色舞地复述完暑假刚读的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《飘》,一位同学非常感慨:“我靠,你这样的人、这样的记忆力,没去上北大,我真替北大可惜!”)
很快,我看闲书的秘密被大人们发现了,除了日常语言泄密外,更让家长、老师恐慌万状的是我成绩的稳步下滑。于是他们开始苦口婆心,劝说我暂时先放下闲书专攻学习,“看闲书对你考大学没好处,考不上大学将来没前途。”温顺怯懦的外表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面具,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听话的小孩,于是我得以阳奉阴违、勇敢执着地走在偷看武侠小说的道路上。
上课时我把《云海玉弓缘》放在课桌下,趁着老师写黑板时偷瞄,我甚至练成了一只眼偷看老师一只眼偷看小说的独门绝技;回家后我把《语文》书皮(那时流行塑料书皮)套在《书剑恩仇录》的外面,在不大识字的老太面前光明正大地看;晚上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“挑灯夜读”《鹿鼎记》,像韦小宝一样智慧巧妙地躲过多方的围追堵截。
除了武侠,《红楼梦》曾一度徘徊在我的生活中,那时我最喜欢林黛玉的“孤高自诩、目无下尘”,讨厌薛宝钗的世故、虚伪。电视也是我那时的最爱,我总是在自己喜欢的连续剧里扮演女主角,坐在荧屏前,与剧中人同欢乐、共涕零。我还给江苏台综艺节目《荧屏与观众》的主持人陈清写过信,表示长大以后如果不能当侠女就做个像她一样优秀的主持人。
与此相反的是,课堂上老师的话永远无法真正打动我。我没有三毛的勇气,虽无心上课,却不敢逃学,只是在每个45分钟的课堂内神游,痴痴地睁着双眼,脑海里浮现我的侠女梦,寻找着冰川天女的宝剑、翠羽黄衫(霍青桐)的足迹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有一次还真的被我梦到了:我一身雪白、身穿羊皮袄裤、头戴羊毛帽子、骑着一匹白马、腰佩一把长剑、一路向西北,我纵马驰骋,很快出了宿迁城,耳边响起呼呼的风声,忽然一道风景出现在我眼前,啊,是我朝思暮想的天山,美妙极了,我哈哈大笑,正准备去拜会青桐姐姐,一不小心笑醒了,才发现只是南柯一梦!
北漂时,《读书俱乐部》的丁老师也迷金庸,空闲时我最爱追问他当年电话采访查老先生的情形,他说,“我好羡慕那些从未读过金庸小说的人:还有那么多部金庸小说没读,该是多么值得期待的人生啊!”
想起丁老师的不朽名言、回忆上学时偷看武侠小说的经历,那种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于头顶的战战兢兢,真是不堪回首。现在的我,可以在夜深人静的今宵、热上一杯牛奶、肆无忌惮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躺着---重读金庸,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?





用户评论()